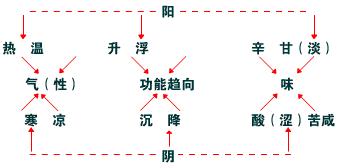第27節 古代房中術縱論

中國的房中書,年代最古老,不僅大大早于印度的《欲經》(Kama
Sutra),而且比羅馬的《愛經》(Ars Amatoria)也早不少。其還精補腦之術可推始于漢,也早于印度的密教。明清的色情小說更冠絕一時,在本世紀以前,不僅數量空前,而且內容也極豐富,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馬克夢(Keith McMahon) 教授說,凡是人腦瓜能想出來的,他們都寫出來了。
在北大的演講中,有一點好象我沒講,這就是我壓根兒也沒想寫一部新書,取高氏而代之。因為老實說,這個領域有三大塊,一塊是房中書,一塊是內丹術,一塊是小說(還有春畫),附帶的情愛、婚姻、家庭、生育,枝枝蔓蔓,也鋪蓋甚廣,我除對房中書有所涉獵,其他方面知識不夠,不想孤軍深入,走的太遠。不過,近來讀過兩篇評論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的新作,心血來潮,倒想說上幾句。
房中書在中國是屬于方技四門之一。這四門雖與醫學有關,但比醫學的概念要廣,不限于消極的防治疾病,還包括積極的養生保健,甚至以服食、行氣、導引和房中為煉養功夫,求益壽延年,通于神明,同古代的神仙家有很大關系。古人所謂“神仙”,本來不過是健康透頂,老而不死的意思,但在道家或道教中,確實有宗教含義。現在科學昌明,大家對最后一條都不大敢講,但又不滿足于西洋醫學概念之狹窄,寧可騎墻于科學、迷信,折其衷曰“養生”。這種態度固不免坐詒“前現代”或“前女權”之譏,滿可以讓新學之士掄圓了耳光照死里抽,然而論者有解固精為“養生”,媚藥、采補為“補養”,指房中術是從“養生”進于“補養”,由“補養”進于“荒誕”,很多批評都不在點上,太多“現代人”的偏見和誤解。例如這位作者說,中國的房中術只講“性”不講“愛”,流于“非道德化的生物學態度”,不如羅馬和印度更多“對性體驗的微妙描述和對情欲的深刻理解”,恐怕就是小題大作。因為世界上的其他房中書,據我所知,他們也一樣是以男性為中心,一樣有這種“生物學態度”,甚至就連最羅曼蒂克的談情說愛,也未見其高潔(況且他們還有不少我們古語所謂“禽獸行”的變態描寫)。比如《愛經》吧,這書雖然是講“愛的藝術”,但它一開篇就講得很清楚,“我們要唱的是沒有危險的歡樂和被批準的偷香竊玉”。它的中心是講“獵艷”,即如何勾引女人、籠絡女人。這不僅有助于了解西方談情說愛的慣用伎倆(如為女人拂去胸頭的塵埃,或替她拾起曳地的裙裾,花言巧語,大獻殷勤,窮追不舍,作尋死覓活狀,等等),也與中國小說中的風月老手如西門慶在手法上可以溝通(我們有撿手絹、做衣服一類糙招)。涉及房事,也有教女人如何投男人所好擺姿勢,沒有高潮也要假哼哼一類秘訣。ヾ還有《欲經》,這書不但和中國的房中書一樣的“不潔”,而且還打著印度宗教和種性制度的深刻烙印,別說“男女平等”,就連“男男平等”或“女女平等”也不講帶有“生物本能”的“荒誕”之處也一點不比我們遜色。如《肉蒲團》寫未央生愧“本錢”不大,請“天際真人”動手術,竟將狗鞭移植于“那話”之中,很令讀者駭怪。這種想象大概就是受外來影響,很有印度特色。因為《欲經》對這類把戲的描寫那才叫淋漓盡致。原始民族喜歡“人體雕塑”,刺面文身、貫耳穿鼻,遺風見于各國,但象印度人拿生殖器(男性的)開刀,橫切豎割、打眼鉆洞、鑲環嵌珠,以為非此不能有“樂”。這種“根雕藝術”好象還比較少見。
中國的房中書是技術書,而且是相當專門的技術書,它的特點是“術語化”和“公式化”形成很早,而且一開始就同文學有分工,只談“性”不談“愛”,追求簡煉精賅,避免拖泥帶水。這是它比較發達的一個標志。現在從文獻著錄和考古發現看,房中書在中國的發現至少不晚于西漢文帝時(公元前100年左右),而且從其成熟和穩定性判斷,還可上溯到更早。我們估計,將來必有戰國時期的文本發現。例如漢文帝時的名醫淳于意,就已從他的同鄉陽慶授讀過此類秘本(“接陰陽禁書”),馬王堆房中書也大抵抄寫于相近的時間。晚一點,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了八種房中書。這些書都已亡佚,但東漢流行的房中書,有道教盛稱的“房中七經”(黃帝的房中書、《玄女經》、《素女經》、《容成經》、《彭祖經》、《子都經》、《陳赦經》),仍有不少佚文保存。比較出土的漢初文本和傳世佚文,我們不難發現,這些書里的問對人物雖換來換去,但談話的內容大同小異,從術語到體系都很相似,可見早已定型。中國的傳統,很多都是兩千年一系相沿不改,例如晚明抄本《素女妙論》,就和漢初的馬王堆房中書連細節都極為相似。
對中國的房中術進行批判,“生物本能”說最不著邊際。我們中國人講“生物本能”,喜歡以“食”、“色”并舉(今痞子呼為“二巴”),但馬王堆房中書《天下至道談》之所以把房術稱為“天下至道”,只是因為“人產而所不學者二,一曰息,二曰食。非此二者,無非學與服”。他們只承認吃飯、睡覺可以不學就會,并不認為“色”也在其中,因而強調“合男女必有則”,因而要把這個“則”當學問來做。在我看來,這正是它很嚴肅、也很科學的地方。王朔的小說有一句話,叫“愛有千萬種,上床是最下一等”。但是西方性學家以為凡上帝不恥于創造的,我們也不恥于言說”。他們的性學手冊講床笫之事,照樣也是舍道德、宗教、婚姻、家庭不談,毫無羅曼蒂克可言。可見在這個“最下一等”上,洋人和我們也是所見略同。要找中國房中書的“毛病”,當然還有許多。例如這類書是以“房中”(猶今語“屋里的”)、“陰道”(也叫“接陰之道”)、“御女”為名,詳于女而略于男(比如講“女有九宮”就比“男有八節”要詳細,連圖都有),就很明顯是以男性為中心。其體裁多依托帝王(由帝王垂詢,而由帶神仙色彩之智者作答),也有很濃厚的多妻制色彩(但并無賤視平民之意)。這些都可以說是切中要害。不過,拙見以為,即使連這樣的東西也不必大驚小怪(見不怪為怪)。因為這類態度以今日看雖不近情理,但在古代卻屬正常。男權在古代的普遍是不用說了。多妻,以西方基督教的標準看是反常,但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。況且即使是西方的傳統,原來也有類似背景。比如1993年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剿滅的柯瑞施(David Koresh),他就是以《舊約》中的大衛王自居,理直氣壯地以“多妻”為正統。《天下至道談》說“句(茍)能持久,女乃大喜,親之兄弟,愛之父母”,當時的人講房中,意義之偉大而止乎此,你還能要他講什么呢﹖中國房中書同道家和道教有密切關系。這種書,早期與晚期不太一樣。早期,兩漢魏晉和隋唐,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類古書,他們雖然往往打著帝王的旗號,但不一定是禁秘之書,反而往往是普及本。這類書與“黃老之術”有密切關系,如《素女經》、《玄女經》、《容成經》就是屬于黃帝書而漢代注釋《老子》也有以方技和房中解老的傳統(如《河上公章句》、《嚴遵指歸》和《老子想爾注》),房中書借《老子》中的詞匯為術語,傳統可以上溯到馬王堆帛書。
但這樣的書,所述多是常識規范,被葛洪譏為“粗事”,魏晉道教對房中術真正看重的是口訣和言外之教。後者見于《黃書》、《仙經》等書,往往都是圍繞“九淺一深之法”、“多御少女莫數寫精”、“還精補腦之術”這三大要領。這類要領雖可溯源于馬王堆房中書,但在操作上大概有許多具體規定,後來有進一步發展。東漢末傳房中術有三個主要派別,一個是傳容成之術(甘始、左慈、冷壽光、東郭延年和封君達,即黃老派的房中術),一個是傳彭祖之術(黃山君),一個是傳玉子(張虛)之術(天門子、北極子、絕洞子、太陰子、太陰女、太陽女)。前兩個派別所傳可能多為“粗事”,但後一派別與“墨子五行術”有關,所述口訣同張陵《黃書》相似,似帶有較多神秘色彩(見葛洪《神仙傳》)。後世內丹術的發展當與這一類秘術修煉和口訣傳授有關。
我體會,上面提到的“從養生到荒誕”,所謂“荒誕”大概主要是指內丹派的房中術。關于內丹術,我并不在行,這里不敢多說,只想講兩點。第一,內丹術在宋以前地位不如外丹,這點與科技水平有關。因為呼吸吐納、屈伸俯仰、男女交接雖然都是最老牌的健身術,但它們皆屬“無本生意”,在“金丹大藥”為“高科技”的時代,自然不被看重。戰國秦漢以來,人們最迷信的是“藥”特別是化學制劑的“藥”(今天的西方仍如此。他們的化學也是源于煉金)。比如葛洪就認為,只有金丹是致仙之本,如藥不成才兼修眾術。他不但不認為憑房中可以“單行而成仙”,還直指其說為“巫書妖妄過差之言”(《微言》)。這是宋以前的主流。第二,現在研究者多已指出,外丹術的衰落是在唐以後,因為唐代吃死了一大批皇帝。房中和其他“無本生意”借這一契機復興,有一大特點,是它們用外丹術語全面改造了原來的體系。新的房中書有各種派別,恐怕要從道教的內在思路去研究,并不能簡單以對女性的恐懼、仇恨或壓榨概括之。這些派別的共同點是進一步技術化,希望借外丹以外的技術達到神仙境界。如果我們從道教外的觀點去看道教,當然可以視其宗教境界為“荒誕”,但這種“荒誕”正唯其是專業體育式的唯技術主義,所以也就和大眾的關系相對的少。宋明以來,房中采戰主要流行于道教內部和宮闈之中(史志不載這類書籍),普通百姓別說花不起功夫賠不起錢,光是老婆太少這一條,就得讓他們望而卻步。我們若以這樣的局部去概
括中國古代的性傳統恐怕不妥。
鑒于上述討論,對中國性傳統的評價,我有一個積極的建議,這就是我們與其拿房中書作標本,對中國的兩性關系做社會學評價或意識形態批判,還不如從中國明清小說入手。因為后者不但比較非技術化也比較世俗,而且有豐富的社會場景,更能反映全局。
中國小說講兒女風情,種類很多,可以“性”、“愛”并舉,也可以只講其中一種。統言之曰“人情小說”,分言之則有許多細別(如“才子佳人小說”、“狹邪小說”和“淫穢小說),從異性到同性,從正常到變態,從閨閣到青樓,從皮肉爛淫到兒女情長,簡直應有盡有。明清之際,市井繁華,人欲橫流。俗話說“飽食思淫欲”,那時的人真是吃飽了撐的,什么都想得出來,有些簡直入于科幻之境。加上中國印刷術又特別發達(比同時期國外印刷物的總量還大),當然最能反映中國性傳統的方方面面。這樣的東西和古代的房中書或道教傳統當然有關,但又很不一樣。例如早期房中書講體位,有十節、九法、三十式,花里胡哨,好象菜譜(一位法國朋友這樣講),但入于小說只有三種,一曰“順水推舟”,二曰“隔山取火”,三曰“倒澆蠟燭”,不但名稱大變,而且數量被簡化,反而是最基本的體位(西
方叫“前入”、“後入”和“女上”)。還有《金瓶梅》等書多有“二八佳人體似酥”一詩,相傳是呂洞賓所作,就是出自道教,但書中所述還是以普通人的一般性生活為主。
對中國古代性生活應當怎么看,高氏之書只是搭了個架子,很多問題還值得討論。特別在女權運動勃興的現在,對高氏之書的“反思”更在所難免。例如近來美國教授費俠莉就已寫出新的評論,并且遭到旅美學人李曉暉的反詰。費俠莉從女權角度抨擊高氏之作,不失為一種新的角度,但她的問題是對史料誤解太多。比如她從房中書可以讀出壓迫婦女,從胎產書可以讀出關心婦女,并以此虛構中國歷史的前后反差和儒道對立,就是屬于“求荒誕而得荒誕”。因為中國的胎產書原與狹義的房中書出于一系,中間并沒有她想象的那種對立。
過去陳寅恪先生給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寫《審查報告》,曾指出研究歷史并不是同古人找茬,尋找他們的可笑之處(這很容易),相反他主張要對古人抱“了解之同情”,我很贊同。但是另一方面,我還有一種陋見,就是今人行事思考,大可不必糾纏于古人,如果你覺得他們不合口味,則束書不觀可也。(柯文輝﹕《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》《讀〈中國古代房內考〉有感》,《世紀》1993年2期52-55頁康正果﹕《從養生到荒誕(房中書透視)》,《讀書》1995年2期46-52頁Chalotte Furth: "Rethinking Van Gulik: Sexuality andReproduction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." in ENGENDERINGCHINA--Women,Culture, and the State, PP. 125-146, edited byChristina K. Gilmartin etc., Harvard, 1994; 李曉暉﹕《千古風流在中華--高羅佩其人、其妻、其藝、其學》
注釋﹕
此書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譯本。戴本是從法文節譯本譯出,刪去其“生物本能”部分。
如《大樂賦》即屬色情文學而不是房中書。同樣,嚴格地講,《愛經》也不是房中書。
例如李小江有“男性經歷了五種社會形態,女性只經歷了兩種社會形態”的怪說,就是著眼于男權統治的普遍。平均妻權要比平均地權難得多。正是從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看,西方在老婆問題上的公平思想才顯得難能可貴,令人敬佩。當然,這仍然只是“形式上的平等”。事實上,他們也是除“正經房子”還有“避雨窯子”,情婦、妓女還是少不了。馬克夢說,他在美國講中國性史,學生最受刺激的就是多妻。西方人對阿拉伯世界的多妻制比較了解,而對中國的知識還太少。古代帝王妻妾成群,疲于應付,是這種書冠以帝王之名的一個理由。另一個理由是他們在古代是緋聞焦點(就像好萊塢影星),正好利用平民之艷羨以為廣告之資。但更大的可能只是在于利用帝王的聲望,就像西方講剖腹產要依托凱撒(日語叫“帝王切剖術”,例如“赤子”,男陰“玄門”,女陰“握固”,閉精“走馬”,射精。
房中雖以水火喻男女,以戰斗喻交接,甚至有“臨深御奔”一類對女性的不敬之辭,但其說蓋主于“慎”,往往先言其害後言其利,并非真的認為“水火不容”、“你死我活”(這可能嗎,而是主張男女兩利,水火既濟。)
- 相關文章
-
沒有相關文章
- 網友評論:(只顯示最新10條。評論內容只代表網友觀點,與本站立場無關!) 【發表評論】
- 綠色通道
- 精彩推薦